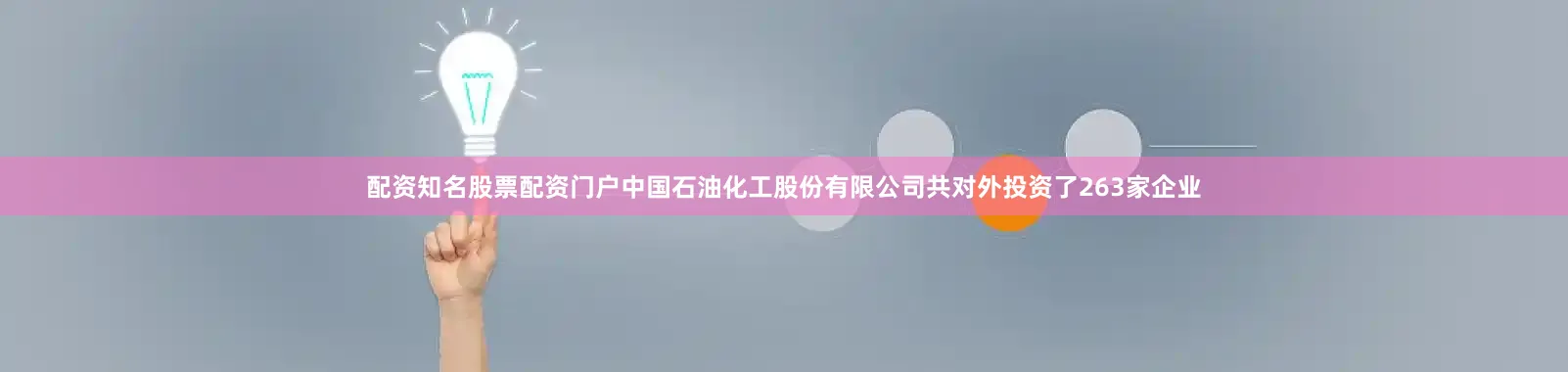青年胡承志
裴文中名片背面的短函
展开剩余90%北平协和医学院旧址
中国地质博物馆展厅中的“北京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北京青年报》和北京市档案学会联手推出“抗战就在我身边”系列报道。在近日的采访中,学会秘书长王兰顺提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遗失。
“北京人”头盖骨具有极高的科学和历史研究价值,其原件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丢失在辗转运往美国保存的途中。当年此事曾轰动国内外,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失踪,不仅是中华文明史难以弥补之痛,也导致了人类演化研究中关键实物证据的永久缺失。而这,完全是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中的悄然失踪,到战后多国多方的持续追寻,其下落始终藏在历史的褶皱里。原件杳无音讯,好在胡承志等留下的模型延续了研究的脉络,档案中裴文中那张背后写着取标本箱的名片、各地探寻记录里的蛛丝马迹,又为这场跨越80余载的寻找埋下了新的伏笔。档案是历史的镜鉴,亦是线索的载体,或许在未来某份未被发掘的档案中,还能找到解开这桩悬案的密码。今天我们重访这段往事,既是对失落国宝的呼唤,更是对历史真相的叩问与铭记,希望依托档案的微光,这颗见证人类演化的“头颅”,终将有穿越迷雾、回归故土的一天。
档案
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人”化石失踪
20世纪20年代起,周口店成为古人类化石发掘的核心区域。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听闻周口店有化石线索后开启考察工作,他敏锐地感觉到:总有一天,这个地点会变成考察人类历史的朝圣地之一。
裴文中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
1927年起,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由北京协和医学院步达生教授主导,我国科学家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等参与,正式对周口店进行大规模发掘。
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在周口店发现了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此后又陆续出土人类化石、石器等,并发现用火遗迹。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周口店发掘因此中断,已发掘的“北京人”化石保存在北平协和医学院(此地是当时存放“北京人”化石的主要地点,因其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挂美国旗,环境相对安全。)
随着太平洋战争阴影的逼近,1941年,日本对中国侵略加剧,为防止化石落入日军之手,经各方反复协商,中方与协和医学院美方人员决定:将“北京人”化石等珍贵标本通过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北平运往秦皇岛,再转乘“哈里逊总统号”轮船送往美国。负责协调此事的有协和医学院解剖科主任魏敦瑞(德裔犹太人,此前研究化石)、院长胡顿、总务长博文、博文的秘书息式白,中方化石研究者如裴文中、胡承志等。他们深知化石的价值,全力推动转移。
1941年11月,“北京人”化石被精心装箱。按计划,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士兵负责运输,先从北平协和医学院运至秦皇岛码头,与当地美方人员交接,再送上“哈里逊总统号”轮船。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消息传至北平,局势瞬间失控。12月8日,驻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被日军全部缴械俘虏,押往天津战俘营,而“哈里逊总统号”因战争爆发未能抵达秦皇岛。那两箱化石,在秦皇岛至天津运输环节,或战俘营转移过程中,悄然失踪。
胡承志是见到“北京人”的最后一位中国人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转运前,由技术员胡承志打包装箱。发出指令的,是协和医学院总务长博文;来通知胡承志正式装箱的,是博文的秘书息式白。可以说,胡承志是见到“北京人”的最后一位中国人。
作家李鸣生著有《寻找“北京人”》一书,他生前曾与胡承志就此事做过细致深入的采访,希望从中摸索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而胡承志作为“北京人”研究与保护的关键实操者,也曾无数次复盘过装箱的前前后后。
装箱事宜启动于1941年4月。魏敦瑞赴美前夕,他找到胡承志,让其把“北京人”和山顶洞人化石装箱,等通知交给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或总务长博文,以便到时交给美国公使馆运往美国。虽然胡承志只是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的一名技士,但已因高超的制作化石模型的技术得到魏敦瑞的欣赏和信任,他接下任务后便时刻等待下一步指令。七八月暑气蒸腾,裴文中找到胡承志,告诉他“北京人”化石要全部装箱运走,听消息做准备。胡承志追问何时装箱,裴文中只回答“听信儿”。
最后的装箱指令来自美方总务长博文。胡承志后来推算时间应是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18至21天,也就是1941年11月中下旬。
装箱现场,胡承志将提前准备好的一大一小两只白木箱摆好,由于装的不是模型,而是真家伙,他每一步都更加小心谨慎。他将化石从保险柜中一件件取出,计有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5个,山顶洞人头盖骨3个,北京人头盖骨碎片数十片、牙齿近百颗、残下颌骨13件、上锁骨1件、上腕骨1件、上鼻骨1件,山顶洞人盆骨7件、肩胛骨3件、膝盖骨3件、下颌骨4件及大量其他珍贵的哺乳动物化石。
为保万无一失,胡承志给每件化石都“穿”了六层衣服:第一层是擦显微镜用的细棉纸,第二层是稍厚的白棉纸,第三层是洁白的医用棉花,第四层是医用细纱布,第五层是白色粉莲纸,第六层是厚厚的白纸和医用布。
化石包好后,胡承志将它们小心翼翼地装入四方形小盒,并用汲水棉花将剩余空间填满,再将小木盒装入木箱,最后用木丝填实。妥善安置后,严密封盖,外面加锁,并在两个木箱外面标注编号CASE1、CASE2。
两个小时装箱完毕,箱子由息式白运往博文办公室。再之后,局势急转直下,日军逼近,美方决策摇摆,化石转移陷入混乱,之后踪迹难觅。
化石丢失后,中、日、美多方都曾展开追查,裴文中、贾兰坡等中国学者更是积极奔走。有人推测,化石可能在天津被日军截留,流入日本民间或军方机构;也有说法称,运输时被混乱中的士兵、百姓误拿,甚至随沉船葬身海底。但无论何种推测,都缺乏实证。
中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在找“北京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北平城内一片欢腾,寻找“北京人”的行动随即展开。中国人在找,日本人在找,美国人也在找。
作为战胜国,中国迅速派出使团赴日本,著名考古学家李济作为使团高级顾问,负责在日本考察和索回被掠走的中国文物,而重中之重,就是查询和找回“北京人”头盖骨。
1946年3月在东京,李济见到了驻日美国海军司令斯脱特,斯脱特的回答使李济十分失望:盟军司令部已经就中国政府此前的要求,根据报端的信息查问过东京帝国大学,回答是,没有任何根据证明“北京人”在东京或者在日本。
除此之外,四面八方的消息在寻找中纷至沓来,但战争造成的信息断层,成了横亘在寻找路上的一道鸿沟,那些本该清晰的环节——谁最后接触过化石?运输车辆的编号是什么?中转仓库的具体位置是哪里?都在炮火和混乱中化作了烟尘。
新中国成立后,寻找行动也在继续,化石可能的下落被梳理出几条路径:
1.战火中损毁。专家们认为化石可能在协和医院地下室被日军毁坏,未及时运走,而且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协和医院地下室并不安全。
2.沉船说。装载在沉船“阿波丸”号或“里斯本丸”号轮船上,随船沉入了大海;在从北平运往秦皇岛途中的“哈里逊总统”号上遗失。这艘船在前往秦皇岛的途中,因受到日舰的追逐,最终在中途被击沉。三者皆无确凿证据。
3.掩埋说。上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夏皮罗在《北京人》一书中披露,曾有一位前海军陆战队成员向他透露,“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曾被转运至天津的美兵营;而在1971年10月21日,负责护送化石出国转移任务的美国医生费利证实,化石曾被安置在天津美兵营6号楼地下室的木板层之下。
还有一个被转移至北京日坛公园掩埋的说法,是基于1996年一个日本老兵的陈述,他声称将化石埋在了距协和医院不远的一处树林中,并在旁边的树上做了划痕标记。我国相关人员随后在日坛公园的树林中找到了一棵带有旧划痕的松树,并在同年6月3日上午开始了正式的发掘工作。然而,当挖掘深度达到2米多时,专家们并未发现任何埋藏物,也没有动土的迹象。经过商议,专家们决定再深入挖掘一段距离,但结果只发现了细黄砂岩。
与故宫文物的命运相比,“北京人”头盖骨的失踪更显特殊。1933年起,故宫1.3万箱文物南迁,虽经战火辗转,最终大多得以保全,其关键在于有完整的运输记录和保护团队。而“北京人”头盖骨的转移因战争突发被完全打乱,既无正式交接凭证,也无连续的目击者,就像被战争硬生生从历史链条中“剜”了出去。幸运的是,当年胡承志制作的“北京人”头盖骨模型被辗转寄往美国,根据这些逼真的模型,有关北京猿人的研究得以继续。
现场
中国地质博物馆有一件“北京人”复制品
“北京人”原件的丢失,使得其复制品弥足珍贵,中国地质博物馆史前生物厅中就展出有一件复制品。日前,记者与王兰顺秘书长一同前往走访。
中国地质博物馆的前身是地质矿产陈列馆,位于北京丰盛胡同3号,紧邻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所。裴文中、贾兰坡等老一辈考古学家都曾在调查所工作,胡承志也是那里的技术人员。
2013年,地质博物馆曾经就胡承志的考古经历对其做过采访,当时老先生已经95岁,工作人员尹超负责录音,他向我们回忆了当时的采访情形。
尹超先打开手机,把三条当时的采访录音放给我们听。胡承志先生的声音已显苍老,耳朵也背,由儿子在旁解释和传话。他对“北京人”头盖骨的丢失及装箱做了简单的重复陈述,之后回顾了头盖骨的复制情况:前两个头盖骨发掘出来后,国内外学者很快便开始了复制模型的工作,由于我们的技术比较落后,这两个头盖骨都是由外国专家复制,使用石膏材料按照1:1的比例制作,每个头盖骨都复制了几个模型。第一个头盖骨模型由英国人德蒙复制,还将其中一个带到了国际学术会议上展示,轰动了当时的学术界;第二个头盖骨破损严重,由德国专家复制,其中一个目前保存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
尹超介绍,1936年,第三、四、五个头盖骨出土后,由胡承志牵头,我国科学家开始着手自己复制,并开创了国内复制头骨内部结构的先河。
胡承志在地质调查研究所有“模型大师”的美称,他1931年到新生代研究室工作时仅十四五岁,一直勤奋好学,不仅很快掌握了英文的听说读写,还学习修化石和制作模型。教他的外国专家本来每次收费十美元,几个月后却不肯再教,原因是“胡太聪明,他现在做的已经比我好了”。录音中,胡承志说到自己的考古目标:希望抓到标本2000种,最终抓到了1000种多一点儿。
犹太科学家魏敦瑞在战前不得不离开北平前,安排胡承志做好了所有“北京人”头盖骨的模型。李鸣生在书中论及此事,由衷感叹其预见性,认为这一举措为日后中外科学家们的研究提供了形象的依据,稍稍弥补了“北京人”丢失的一些遗憾,为此,全人类都应该向他们致敬。
访谈中,王兰顺还谈到一件事,并重点向地质馆的同仁们做了询问。他曾在北京档案馆查到一份档案,是裴文中的一张名片,名片背后是写给舒捷民的短信,说“派工友胡君前去取回存在贵府的16个标本书物箱”,落款时间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王兰顺说,胡君即胡承志,舒捷民即舒壮怀,捷民是他的字,日伪时期任北平工务局局长。王兰顺提出的疑问是:裴文中嘱胡承志去取的这16箱标本中会不会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16箱标本现在下落如何?有可能在地质馆吗?
地质馆工作人员介绍,曾于2019年至2021年进行了全面清库工作,对遗留库存全部做了整理,没有发现过那一时期的标本化石,当时装物品的包装箱也都处理掉了。尹超回忆,胡承志在2013年的采访中也没有提及曾被委派去接收文物标本的事。那么,裴文中要取回的那16箱化石标本的命运如何?是否真有可能包括“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如今这也已成了一桩悬案。
本版文/本报记者王勉
档案供图王兰顺
发布于:北京市倍悦网-炒股怎么配资-正规的配资炒股平台-股票配资交流论坛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